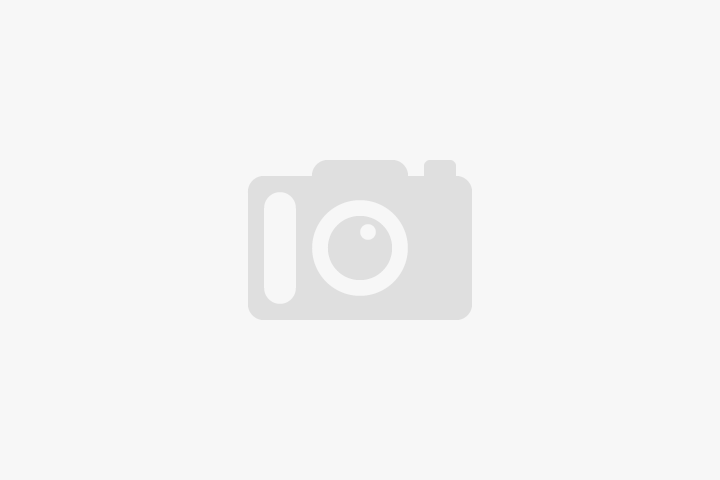微信扫一扫
我把西海岸的历史说给你听

至秦汉时期,
琅邪郡成为滨海强郡;
千年古港——琅邪港,
也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生与
繁荣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孕育了辉煌的古代青岛海洋文明。
今天起,
小编和你们一起走进古琅邪、感受古琅邪,
重温那段激荡人心的历史。
二
岁始琅邪——秦汉滨海强郡
秦王嬴政灭齐国之后,在原齐国琅邪邑的基础上设立了琅邪郡。刘邦建立汉朝,仍设琅邪郡。很长一段时间,秦汉琅邪郡治所在地即在琅邪台附近。秦汉时期,皇帝登临琅邪台,能够提供大规模船队出海的琅邪港和琅邪郡城共同进入了辉煌时代。
1
琅邪台与徐福东渡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11年中,“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先后对全国进行了5次规模宏大的巡幸,以显赫其威严与“功德”,进而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在这5次巡幸活动中,除第一次西巡和第四次北巡以外,其余3次均到过琅邪。
☟
第一次到琅邪是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此为始皇第二次出巡,“东行郡县”,途经邹峄山、泰山、之罘等地,南登琅邪,“大乐之”,居留三个月。迁徙居民3万户于琅邪台下,并免除其徭役12年,大兴土木,重修琅邪台,并于台上刻石立碑,颂秦功业。始皇此行还受“长生不死”迷信观念的驱使,不惜代价,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始皇帝二十九年(前218),第三次出巡,经阳武、之罘,再次登临琅邪。
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第五次出巡,也是始皇帝最后一次出巡,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少子胡亥随行,经云梦、丹阳、钱唐、会稽、江乘等地,第三次来到琅邪。此间,方士徐福因入海求神药数年不得,诈称海中有大鲛鱼作祟,船不能行。“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便令入海者怀抱捕巨鱼具,并亲执连弩,等待巨鱼出现。自琅邪北至荣成山,未见巨鱼。及到之罘,方见大鱼出没,射杀一条。后取道临淄西归,归途中始皇病死于沙丘平台。
汉武帝第一次登游琅邪是在元封五年(前106)的冬天,他带领文武百官,海陆兼行,一路礼祀名山大川。《史记》记载这次巡幸为:“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昔秦始皇曾“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祠“四时主”于琅邪。武帝此次登琅邪,主要也是祭祀“四时主”神,并游览名胜琅邪台。
武帝第二次幸琅邪为太始三年(前94)春二月,也是海陆兼行。《汉书》记载此行为:“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
关于徐福东渡,一般认为是从琅邪起航。而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击败匈奴、修长城时,还从琅邪等“负海之郡”运送军粮至河北。琅邪港成为重要的运输港口,其吞吐量不可小视。以琅邪郡古港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航海事业和航海文化,是中国人进军海洋、探索自然的重要起点,是中国作为海洋的大国的历史渊源之一。
徐福,一作徐巿,秦琅邪人,字君房, 方士。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上书秦始皇并受派遣,出海采仙药,最后“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前219年、前210年,以徐福航海为代表的秦人东渡日本,是中外航海史上的惊世壮举,展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航海领域中所居的领先地位,揭开了古代中国人跨境远航的序幕,是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航海活动。徐福航海的深远影响,不仅加快了日本韩国的社会历史进程,而且开启了东北亚文化融合,可以说琅邪郡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之一,为后世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至今,黄岛地区尤其是琅邪台附近还有众多秦汉遗存。
1973年对琅邪台遗址进行全面普查以来, 文物考古部门曾对琅邪台遗址进行过数次考古工作。2015年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对琅邪台遗址进行了首次大规模而系统的考古勘探调查工作,本次考古工作前后历时36天,取得了丰硕成果。
1.基本确认了琅邪台大台夯土堆积的分布范围(图1)。其平面大致呈“T”字形,“T”字一横位于台顶, “T”字一竖为台顶向南部延伸,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夯土层大致可划分为三层平台,似可与《水经注》载“〔琅邪〕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里,傍滨巨海,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相对应。(图2)
▲图1:琅邪台遗址夯面上的夯窝痕迹
▲图2:琅邪台夯土剖视面
2.在琅邪夯土台北坡,新发现两处长夯土坡状遗迹(图3),一处叠压于新建“御路台阶”之下,一处大致与之平行,均与台顶夯土相连接。以“御路”西发现长夯土坡东西两面皆为深沟,因雨水冲刷侵蚀,形成明显的剖面,夯层历历可见。约当夯土坡中部,有一处石砌构筑物,剖面呈梯形,与往下延伸的夯土坡相连接,当是起维护支撑夯土的作用。该石砌构筑物与1993年发现的所谓“塔形构筑物”形制基本相同,推测与夯土层为同一时期遗迹。另,据《水经注疏》载:“台下路有三,阔三四丈,皆人力为之,今仍呼‘御路’。盖瓦级砖,随在多有。”在勘探中,在此二处夯土遗迹附近也采集到较多的砖瓦碎片,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土人称道的“御路”。
▲图3:琅邪台遗址长坡状夯土遗迹
3.在琅邪山北部,还发现五处夯土遗迹,大致沿山坡而下至山脚。这五处夯土遗迹各呈台状,上下可串联起来,与台顶夯土遥相呼应。可能为当年一处登临台顶的道路,因水土流失等原因,至今残缺不全。
4.琅邪山周边的勘探中,在山脚北发现一处周代遗址,破坏较严重,保存面积约2000平方米。地表可见少量周代绳纹陶片。经过勘探,文化层堆积最厚约1米。
5.确认了琅邪台附近琅邪台大台基(图4)的夯土分布范围。根据勘探可知,其平面呈不规则形状,面积26000余平方米。在大台基遗址还发现陶制排水管道遗迹。(图5)该遗迹位于一处残存夯土台的东南角底部,暴露的单排陶管北高南底,大致正北往正南方向铺设。每节陶管长约0.68、粗端径0.28、细端径0.25、壁厚约0.1米,(图6)其形制规模比在大台发现的陶管要小得多。
▲图4:琅邪台大台基南面远景
▲图5:大台基陶管道及其上部夯土剖面
▲图6:大台基陶管道遗迹平面图
陶管道遗迹
1993年和2012年相继在琅邪台发现,共两处,分别植埋在1-2米深的地表下面。其中一处叠压于环山公路下,露出剖面可见,今已加玻璃罩保护。2012年新发现的陶管道为三组并排长圆陶筒两两套接式南北向排列的管道。(图7)粗端在南,细端向北,南高北低。陶管黄褐陶质,长约55、粗榫端外径45、细榫端外径35、壁厚约5厘米。2012年抢救性清理完该遗迹,拍照绘图后采集了1件标本(图8),其余均回填保护。
▲图7:2012年抢救性清理陶管道遗迹
▲图8:陶管道正视图
塔形石砌构筑物(图9)
位于新修登山“御路”东侧,1993年修筑“御路”时发现。“构筑物”用当地的黄石块砌筑,呈塔形,暴露地面部分正面底长4、顶长3米,侧面部分底长3、顶长2.5米,其用途不明,疑为护土坡。(图10)
▲图9:1993年发现石砌“塔形构筑物”
▲图10:石砌构筑物剖面
琅邪台刻石
现存刻石高129、宽67.5、厚37厘米。石质为石灰岩,色黝青,纹理彻。刻辞13行,86字,其中首行2字,二行5字,三行7字,四、五、六、七行各8字,八行4字,九行8字,十行9字,十一、十二行各8字,末行3字,秦丞相李斯篆书。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刻石之一,世称秦篆之精品。内容为秦二世元年东行郡县至琅邪台,在始皇所立刻石旁加刻之诏书,以彰明先帝功德。北宋年间,苏轼在《书琅邪篆后》记曰:“……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俱在。”明万历年间,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将残存刻石镶嵌。后经历代官府加以保护,留存至今。解放后,刻石移置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移置中国历史博物馆(图11),黄岛区博物馆藏清代刻石拓片(图12)及刻石复制品。
▲图11:国家博物馆藏琅邪台刻石照片
▲图12:黄岛区博物馆藏琅邪台刻石拓片


-
诚聘闸料人员一名
5000-8000元 其他详情五险公积金带薪年假青岛崎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
诚聘3D制图一名 女
3000-5000元 机械制图员详情五险公积金带薪年假青岛崎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
诚聘集装箱车司机经验不限
8000元以上 司机详情青岛金丰益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
诚聘店员经验不限
3000-5000元 店员详情隆鑫华五金机电批发部 -
诚聘操作打磨工经验不限
5000-8000元 操作工详情五险公积金工作餐青岛祥杰橡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
招现场快剪老师
面议 其他岗位详情帧时光数字内容制作服务工作室 -
螺蛳粉店诚聘店长经验不限
面议 店长详情五险年终奖工作餐我爱螺螺蛳粉 -
诚聘app试用员
面议 系统管理员/网管详情鹏力网络 -
招A2驾驶员10人 待遇优厚
8000元以上 司机详情青岛龙泽顺汽贸有限公司 -
电动车配件 诚聘 发货员 理货员 月工资5000以上
5000-8000元 其他详情工作餐顺风电动车配件城 -
电动车配件 诚聘送货司机 底薪加提成 5000-9000元
8000元以上 司机详情工作餐顺风电动车配件城 -
1w+诚聘CNC加工中心操作工
面议 CNC工程师详情五险青岛晟豪
-
上一条:青岛西海岸新区博物馆馆藏铜席镇
-
下一条:青岛西海岸新区博物馆馆藏玉摆件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